男女主角分别是李信李斯的其他类型小说《大秦的血与火后续》,由网络作家“爱吃菜的木木”所著,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本站纯净无弹窗,精彩内容欢迎阅读!小说详情介绍:我叫李斯,我在火光中与大秦的荣耀和罪孽一起埋葬。1蕲南的秋阳像块被磨钝的青铜镜,照得人眼眶发涩。我蹲在王翦的中军帐外,用指尖拨弄着地上的蚂蚁——它们正排着队搬运半粒粟米,像极了咸阳街头运送粮草的车队。帐内传来瓷器碰撞声,李信的声音突然拔高:“末将愿率二十万大军,旬月内必取项燕首级!”王翦的回答低沉如老松拔节:“楚地水泽密布,我军轻装急进,粮草如何接济?”话音未落,帐帘被猛地掀开,李信的青铜头盔擦着我鼻尖掠过,穗子上的血珠溅在我手背,像朵瞬间绽放的小花开在苍白的皮肤上。“廷尉大人,”他冲我甩了甩剑柄上的红缨,甲胄上的鱼鳞纹还沾着晨露,“您说说,我大秦锐士何时怕过攻坚?”他身后的亲兵捧着地图,边角被汗水洇出深褐的云纹,正是我昨日让人加急...
《大秦的血与火后续》精彩片段
我叫李斯,我在火光中与大秦的荣耀和罪孽一起埋葬。
1蕲南的秋阳像块被磨钝的青铜镜,照得人眼眶发涩。
我蹲在王翦的中军帐外,用指尖拨弄着地上的蚂蚁——它们正排着队搬运半粒粟米,像极了咸阳街头运送粮草的车队。
帐内传来瓷器碰撞声,李信的声音突然拔高:“末将愿率二十万大军,旬月内必取项燕首级!”
王翦的回答低沉如老松拔节:“楚地水泽密布,我军轻装急进,粮草如何接济?”
话音未落,帐帘被猛地掀开,李信的青铜头盔擦着我鼻尖掠过,穗子上的血珠溅在我手背,像朵瞬间绽放的小花开在苍白的皮肤上。
“廷尉大人,”他冲我甩了甩剑柄上的红缨,甲胄上的鱼鳞纹还沾着晨露,“您说说,我大秦锐士何时怕过攻坚?”
他身后的亲兵捧着地图,边角被汗水洇出深褐的云纹,正是我昨日让人加急抄绘的《楚地山川图》。
我起身掸去衣上尘土,触到怀中那卷嬴政的密诏,桑皮纸上的朱砂印还带着温热。
“老将军久经战阵,自然有老成谋国之算,”我故意将“老成”二字咬得极重,看见王翦扶着帐杆的手指骤然收紧,“不过陛下昨儿送来的密报说,项燕在城父一带的兵力已不足十万。”
帐内突然静得能听见胡杨林里的风声。
王翦的瞳孔缩成针尖,盯着我腰间晃动的玉珏——那是嬴政亲赐的信物,雕着展翅的玄鸟,寓意“天命所归”。
他身后的帅案上,摆着半块啃剩的麦饼,硬壳上还留着齿印,旁边铜碗里的豆粥结了层油皮。
“既然如此,”王翦忽然笑了,眼角的皱纹挤成深沟,“那就依李将军所言,明日卯时出兵。”
他伸手取过案头的虎符,青铜表面磨得发亮,能照见他眼底跳动的血丝。
李信猛地跪下,铠甲磕在夯土上发出闷响,我注意到他膝盖处的皮革磨出了毛边,显然是常年跪坐所致。
夜半时分,我被帐外的马蹄声惊醒。
月光从毡帐缝隙钻进来,在地上织成银线。
王翦的影子突然笼罩过来,他手里提着酒壶,腰间没挂佩剑,只插着支刻满咒文的木简——那是他出征时必带的楚地巫器,说是能镇住战死的孤魂。
“长卿可知,”他往我面前的陶碗里倒酒,粟米酒的香
气混着血腥味,“项燕的祖父项渠,当年与我在函谷关外对峙时,曾送我一坛楚酒。”
他指腹摩挲着酒壶上的蟠螭纹,壶嘴磕在碗沿发出轻响,“酒坛上刻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我当时笑他夜郎自大,如今……”他没说完,仰头灌下一口酒,喉结滚动时,我看见他颈侧的伤疤在月光下泛着青白——那是与项渠交战时留下的箭伤,险些要了他的命。
帐外传来更夫敲梆子的声音,“天干物燥,小心火烛”的喊声被风吹得七零八落,像极了白天看见的断箭。
卯时三刻,秦军准时开拔。
李信的先锋军穿着新髹的黑甲,甲片间露出的红色里子像流动的血。
我骑着嬴政赐的大宛马,马蹄踩过带霜的草叶,发出细碎的咔嚓声。
远处的钟离山在晨雾中若隐若现,山腰处的隘口像只微张的虎口,等着吞下猎物。
“看!”
身旁的骁将突然指向天空。
一群寒鸦正从山后掠过,翅膀拍打出暗沉的云。
王翦的副将冯劫勒住马,手按在剑柄上:“此乃凶兆,大帅是否……闭嘴!”
我厉声打断他,战马受惊般前蹄扬起,“大秦锐士,岂可信这些山野巫祝之言!”
话音未落,前方突然传来闷雷般的战鼓声,不是一声,而是千万声,从山坳、从河谷、从每一片看似平静的芦苇荡里炸开。
李信的大旗在队伍前方剧烈晃动,我看见他转头时,头盔上的雉羽扫过面颊,划出一道血痕。
楚军的黑色战旗像潮水般漫过山头,项燕站在高处,身披的犀甲在阳光下泛着幽蓝,手里握着的正是当年差点要了王翦命的那柄青铜剑。
“是伏击!”
冯劫的声音带着哭腔,他的马被流矢射中眼睛,原地打转时撞翻了身后的弩车。
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耳中轰鸣,像擂鼓般震得太阳穴突突作痛。
秦军阵脚大乱,前排的弩手还没来得及上弦,就被楚军的投石机砸成肉泥。
我的战马被绊倒,整个人摔进泥水里。
刺鼻的血腥味混着腐草味钻进鼻腔,我摸到腰间的佩剑,却发现剑鞘不知何时已丢失。
身旁躺着个年轻士兵,喉管被割断,双手还紧紧攥着半块烙饼,眼睛瞪得滚圆,倒映着天空中纷纷扬扬的箭雨。
“往回撤!”
王翦的吼声穿透硝烟,他骑着
那匹著名的乌骓马,手中长戈上下翻飞,每一次挥击都带下一片血肉。
我看见他胸前的护心镜已被砍出缺口,露出里面暗红色的软甲,那是他儿媳亲手缝制的,绣着密密麻麻的“平安”二字。
一支箭矢擦着我耳际飞过,尾羽扫过脸颊时,我突然想起咸阳宫里的编钟——此刻战场上的金铁之音,与宫宴上的雅乐并无不同,只是前者奏的是生离死别,后者唱的是太平盛世。
李信的身影在不远处闪过,他的大旗已断成两截,正被楚军的步卒追赶,甲胄上的漆片剥落,露出底下斑驳的旧伤。
黄昏时分,残军终于退到涡水河畔。
王翦坐在一块被炮火熏黑的巨石上,任由军医为他包扎手臂的伤口。
他看着对岸燃烧的营寨,眼神空洞得像口枯井。
我跪在他面前,喉间腥甜难抑:“老将军,是我……是我误判了敌情。”
他抬手止住我,指尖的血滴在我衣襟上,绽开朵暗红的花。
“不怪你,”他的声音沙哑如磨损的竹简,“陛下要的是速胜,是彰显大秦威德的捷报,而我们……”他顿了顿,望向天际最后一抹晚霞,那颜色像极了楚地的丹砂,“不过是棋盘上的棋子罢了。”
夜幕降临,河面上漂满尸体,像秋天的落叶般顺着水流打转。
我摸出怀中的密诏,火光中,嬴政的字迹依然凌厉如刀:“李信果勇,当可大用。
若王翦怯战,可换蒙恬代之。”
纸页在风中簌簌作响,我想起出发前嬴政拍着我肩膀说的话:“长卿,你当为朕的眼睛。”
王翦突然剧烈咳嗽起来,咳出的血沫溅在密诏上,将“天命所归”四个字染成暗红。
我慌忙扶住他,触到他后背嶙峋的骨骼,像触到一段即将风化的枯木。
远处传来楚人的号角声,悠长而苍凉,像在为这场屠杀送行。
“知道为何楚人总也杀不尽么?”
王翦忽然轻笑,手指蘸着自己的血,在石头上画了个歪扭的“楚”字,“因为他们的根扎在泥土里,在《诗》《书》里,在每一个能歌善舞的巫祝身上。
你烧了竹简,却烧不掉他们的魂。”
我望着他画出的“楚”字,血痕正在夜色中渐渐干涸,像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
河风带来远处的童谣,隐约是楚人悼念战死英灵的《国殇》。
王
翦闭上眼,任由血迹在石上蜿蜒成河,而我知道,这场败仗,不过是大秦辉煌表象下第一道裂痕,更深的伤,还在后面。
夜深了,星星从云层里探出头,像极了战场上未瞑的眼睛。
我握紧手中的密诏,直到指甲将纸页戳出窟窿。
王翦的话在耳边回响,与嬴政的训示混在一起,织成一张让我窒息的网。
或许,从踏上这片土地开始,我们就已经输了——不是输在兵力,而是输在不懂,有些东西,比钢铁更坚韧,比火焰更绵长。
但此刻,我只能将这些念头压进心底,就像将带血的竹简藏进袖中。
明天,还要向嬴政写那封注定谎言连篇的捷报。
而蕲南的土地,会记住所有的真相,在每一颗埋下的种子里,在每一滴渗入地下的鲜血中,静静等待着破土而出的那一天。
2阴山的风像把生锈的刀,割得人脸颊生疼。
我站在烽火台上,脚下的城砖还带着烧制后的余温,砖缝里嵌着未洗净的草屑,那是民夫们和泥时掺进去的——为了让泥浆更有黏性,他们不得不把自己仅有的口粮磨成粉,拌进土里。
蒙恬披着件褪色的羊皮氅走来,氅角上结着冰碴,每走一步都发出细碎的脆响。
他递来的马奶酒皮囊上结了层薄霜,我接过时,指尖触到皮子上凹凸的刻痕,凑近一看,竟是某代匈奴单于的名号。
“尝尝,”他的声音被风扯得零散,“这是上个月从匈奴右贤王帐里缴获的。”
酒液入口像烧红的铁条,顺着喉咙滚进胃里,却暖不了被寒风吹透的骨头。
我望着远处蜿蜒的长城,它像条被剥了皮的巨蟒,在群山间扭曲伸展,城墙上密密麻麻的民夫如同附在蟒身上的蝼蚁,正用血肉之躯把它喂得越来越长。
“第三段城墙又塌了,”蒙恬突然开口,手指向西北方,那里的天空飘着几缕黑烟,“压死了三十七个兄弟。”
他说“兄弟”时,喉结重重滚动,我这才注意到他左耳垂上挂着枚铜哨,样式古朴,像是中原的旧物。
“不过是些……”我话未说完,就被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打断。
转头望去,两名民夫正抬着块足有千斤重的条石,竹制的抬杠突然断裂,条石滚落,砸中了后面的少年。
少年的腿骨发出令人牙酸的脆响,他抱着
断腿在地上翻滚,周围的民夫却不敢停下,只能绕开他继续搬运,唯恐监工的皮鞭落在自己背上。
蒙恬猛地扔下酒囊,皮靴踩在城砖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他三步并作两步冲下烽火台,腰间的佩剑在奔跑中磕在城砖上,迸出几点火星。
我看见他推开监工,亲自蹲下查看少年伤势,粗粝的手指轻轻拨开少年染血的裤腿,动作比我见过的任何太医都要轻柔。
“去取草药和夹板!”
他冲亲兵怒吼,声音里带着我从未听过的颤抖。
亲兵愣了一瞬,才慌忙跑向军医帐。
蒙恬脱下自己的羊皮氅,垫在少年身下,氅角的冰碴融化,在少年破烂的衣裤上洇出深色的印子。
“将军,”我跟在他身后,忍不住开口,“这样会坏了军法。
这些民夫不过是……不过是蝼蚁?”
蒙恬突然转头,眼中有怒火在跳动,却在看清我脸色时,忽然软了下来,“长卿,你看这长城,”他抬手抚过城砖,指尖蹭上一点暗红,不知是泥渍还是血迹,“每一块砖下都埋着一具白骨。
可你知道吗?
去年冬天,有个民夫临死前,还在砖上刻了自己妻子的名字。”
他从怀里摸出块碎砖,递给我。
砖面上果然有歪歪扭扭的刻痕:“阿芳亲启”。
四个字刻得极浅,却穿透了砖面,能看见里面夹杂的稻草碎屑。
我想起咸阳宫的地砖,每一块都打磨得光滑如镜,刻着云纹和瑞兽,却从没有哪一块,藏着这样的体温。
“他们不是蝼蚁,”蒙恬的声音低沉如远处的闷雷,“他们是大秦的子民,是替陛下守护边疆的人。”
他顿了顿,望向天际的雁群,它们正排成人字往南飞去,“你总说法治至上,可若是连人都不爱惜,法又有什么意义?”
我握紧那块碎砖,棱角扎得掌心生疼。
远处传来监工的呵斥声,又有几个民夫因为动作迟缓被鞭笞。
鲜血溅在城砖上,与之前的暗红融为一体,分不出哪滴是哪个人的。
蒙恬站起身,从腰间解下那枚铜哨,放在少年掌心:“吹这个,以后没人敢欺负你。”
<少年茫然地望着他,眼角还挂着泪珠。
蒙恬轻轻替他擦掉眼泪,动作像极了我见过的他抱孙子时的模样。
我忽然想起,他的长子蒙毅曾对我说过,蒙恬
在家中从不摆将军架子,甚至会亲自给孙子编蝈蝈笼。
“长卿,”蒙恬重新披上羊皮氅,氅角的冰碴已经化了,显出底下黯淡的红色——那是被鲜血染过的颜色,“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
在咸阳宫的演武场,你穿着儒生长衫,却敢站在秦军阵前谈法治。”
我当然记得。
那时我刚入秦,满腔抱负,在演武场看见蒙恬训练士兵,便直言不讳地批评他“过于仁厚,难立军威”。
蒙恬却只是笑笑,让士兵给我搬来胡床,还让人煮了羊肉汤给我驱寒。
“有些东西,”他望着绵延的长城,声音被风吹得断断续续,“比权力更重要。
比如人心。”
他突然剧烈咳嗽起来,我这才发现他咳出来的痰里带着血丝——去年他在北疆中了匈奴的毒箭,虽说捡回条命,却落下了病根。
夜幕降临时,我独自登上烽火台。
月光给长城镀上一层冷银,远处的民夫们还在劳作,火把连成一条蜿蜒的火龙,像极了当年蕲南战场上的楚军篝火。
我摸出怀里的《商君书》,书页间夹着蒙恬给我的碎砖,“阿芳亲启”四个字在月光下若隐若现。
风忽然大了,卷着沙砾打在城砖上,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极了焚书时竹简爆裂的声音。
我想起淳于越临死前的眼神,想起王翦说的“楚虽三户”,想起嬴政在沙丘平台的眼泪。
原来所有的铁血与强权,都抵不过一个民夫刻在砖上的名字,抵不过蒙恬眼中的慈悲。
烽火台的角落里,堆着几具尚未掩埋的尸体,其中一个少年的手紧紧攥着什么。
我掰开他的手指,发现是粒干瘪的粟米,大概是他藏了很久的口粮。
月光落在他脸上,那是张顶多十五岁的脸,眉骨间却已有了成年人的沧桑。
我站起身,将《商君书》放在他胸口,用碎砖压住。
风掀起书页,露出“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句子。
或许商君当年也没想到,他的法治会变成今日的酷政,他的“匹夫”会变成“蝼蚁”。
远处传来蒙恬的口令声,士兵们开始换岗。
我望着月光下的长城,忽然觉得它不再是帝国的屏障,而是一条锁链,锁住了天下人的心。
而我,曾是这锁链的锻造者之一,如今却在这寒夜里,听见了锁链下传来的心跳声
——那是千千万万被视为蝼蚁的人,依然鲜活的心跳。
黎明时分,我看见蒙恬骑着马巡视工地,他的羊皮氅在风中猎猎作响,像面破旧却依然飘扬的旗帜。
某个民夫突然摔倒,他立刻翻身下马,扶起那人,还从怀里掏出块干粮递过去。
周围的民夫们看着这一幕,眼里闪过我从未见过的光,那不是恐惧,而是希望。
我摸了摸腰间的玉珏,“受命于天”的刻纹在晨光中显得有些刺眼。
或许蒙恬是对的,真正的强大,不是用恐惧筑起高墙,而是让人心甘情愿地为你筑起城墙。
而我,似乎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样的光了——在嬴政的眼里,在赵高的眼里,甚至在我自己的眼里。
转身离开时,我听见身后传来少年的笑声——那个断腿的少年,正用蒙恬的铜哨吹出不成调的曲子。
哨音混在风声里,却显得格外清亮,像初春的第一声雁鸣,刺破了漫长的寒冬。
或许,在这钢铁与血肉的长城之下,还有些东西,是永远无法被摧毁的。
3青铜兽首烛台上,十六支牛油烛正滋滋燃烧,蜡泪凝结成蜿蜒的白蛇,顺着雕龙刻凤的烛台底座爬向地砖。
我跪在丹陛之下,膝盖隔着玄色朝服仍能触到石砖的冷硬。
抬头望去,嬴政的十二旒冕正随着他的呼吸轻轻晃动,翡翠珠串后那双眼睛,像极了渭水冰面下蛰伏的鳄鱼。
“李斯。”
他的声音裹着鼎中烹煮的椒艾香气砸下来,我注意到他按在青铜龙纹案几上的右手,拇指正一下下摩挲着案角——这是他惯有的小动作,每当斟酌言辞时,指尖便会无意识地寻找坚硬之物。
“六国已灭,天下初定。
你且说说,如何治理这万里江山?”
我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
三个月前在函谷关外,我亲眼看见他用同样的眼神凝视着六国地图,指尖划过楚国疆域时,指甲盖都因用力而泛白。
此刻这双眼睛里跳动的,是征服者的火焰,亦是守业者的狐疑。
“陛下,”我解开腰间玉珏,任由它坠在阶前发出清越声响,“周室衰微,诸侯混战,皆因分封制尾大不掉。
今陛下神武,荡平六合,当废分封,立郡县。
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
如此,地方官吏皆由陛下任免,财赋兵甲尽归朝廷,方能永绝割
据之患。”
殿内响起衣料摩擦的窸窣声。
我用余光瞥见,右首列位的博士淳于越正攥紧袖口,露出半截竹简角,青黑色的编绳上沾着陈年墨渍——那是他总带在身边的《春秋》,连如厕时都要捧读的鲁国旧典。
“臣有异议!”
淳于越的声音像被霜打了的稷穗,却硬是梗着脖子往前跨了三步,腰间玉佩撞在石阶上迸出脆响,“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
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若朝堂生奸佞,如田常、六卿之流,无宗室拱卫,何以相救?
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他说到“师古”二字时,特意提高了声调,袖口的竹简滑出寸许,我看清了简首朱笔写的“隐公元年”。
嬴政的冕旒突然剧烈晃动,烛火在他瞳孔里碎成金箔,我知道这是暴怒的前兆——七年前,他在蕲年宫听见“太后男宠”四字时,眼中也曾闪过这样的碎光。
“陛下,”我猛地叩首,额头撞在砖缝里嵌着的碎玉上,腥甜在舌尖漫开,“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
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
臣闻市井小儿皆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此等妖言,皆因旧典未毁,人心未一!”
淳于越的脸色瞬间褪成羊皮纸色,他腰间的玉佩终于不堪撞击,“啪”地碎成两半。
我看见他喉结滚动,像要咽下破碎的牙齿,却在开口前被嬴政的冷笑截断。
“准奏。”
嬴政抬手按在剑柄上,龙渊剑的鱼肠纹在烛火下泛着幽蓝,“非秦记皆烧之,敢藏《诗》《书》者弃市。
至于淳于博士..……”他顿了顿,冕旒下掠过一丝玩味,“可留你全尸,归葬曲阜。”
淳于越猛然踉跄着跪下,白发散落在玉碎上,像冬雪落在残棋棋盘。
我站起身时,发现自己的朝服下摆已被烛泪浸透,凝成硬块。
殿外忽然刮起西风,卷着阶下的碎玉片直扑丹陛,被武士的戈矛挡成一片晶亮的雨。
退朝时,王翦的青铜铠甲声从身后传来,像晒干的豆荚在风中轻颤。
这位三朝老将的右肩比左肩低了半寸,那是二十年前抗燕时中箭留下的旧伤。
他身上还带着北疆的霜气,与殿内的椒香混在一起,生出一股腐朽的
甜。
“长卿,”他在廊下停住,苍鹰般的侧脸被暮色切出冷硬的轮廓,“你可知,这把火会烧掉多少文明?”
他抬手往殿外一指,我看见远处的兰池宫正在暮色中下沉,廊柱上的漆画被火光照得明明灭灭,那是上周刚让人重绘的《大禹治水图》。
“老将军,”我解下被烛泪弄脏的玉佩丢进廊下积水,看着它沉向游鱼不惊的池底,“乱世需用重典。
当年您灭楚时,可曾顾惜过郢都的编钟雅乐?”
王翦的喉结动了动,我这才发现他鬓角新添了大片白发,像秋霜落在老松枝头。
他转身时,铠甲上的铜片相互撞击,惊起一群栖息在廊檐下的蝙蝠。
那些灰扑扑的影子扑棱着掠过我眼前,我突然想起蕲南战场上,楚军的黑色战旗也是这样遮天蔽日地压下来。
“项燕自刎前,”王翦的声音从阴影里飘来,“曾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当时我以为不过是败军之将的妄言,如今看来..……”他没有说完,脚步声渐远,只留下一串潮湿的血点——他的旧伤又在渗血了。
我站在廊下,直到月亮爬上椒房殿的飞檐。
远处传来太仆寺的马嘶,夹杂着隐隐约约的竹板声——那是宫正署在责罚失仪的宫人。
袖中传来竹简的棱角触感,我这才想起今早塞进袖口的《商君书》残卷,书页间还夹着一片楚国的橘叶,是去年使者从故楚郢都带回的贡品。
指尖摩挲着橘叶的纹路,我忽然想起淳于越被拖出殿时,眼中那团将熄的火。
咸阳宫的夜风吹散最后一丝烛香,我摸出腰间新换的玉珏,在月光下看清了匠人新刻的铭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珏身冰凉,刻痕却硌得掌心生疼,像极了嬴政方才按在我肩头的力道——那看似轻柔的一按,实则藏着让我必死的决心。
深吸一口气,我将橘叶揉碎扔进池子里。
游鱼受惊般散开,水面倒映的冕旒碎成千万片,又在涟漪平息后重新聚成嬴政的脸。
他永远都在那里,在玉珏的铭文里,在燃烧的竹简中,在每个秦人仰望的方向。
而我,不过是他手中的刀,是这架庞大机器里的一枚铜钉,无论愿意与否,都必须钉进历史的石壁,任岁月将棱角磨成齑粉。
转身走向府宅时,街角传来童谣声,几
个孩童拍着手唱:“一法度,衡石丈尺。
车同轨,书同文字..……”我摸了摸袖中的《商君书》,忽然想起商鞅被车裂那日,咸阳百姓也是这样唱着新法的条文,却在他断气后一哄而上争抢他的血肉。
夜更深了,远处的焚书台已垒起丈高的柴垛。
明天,那些承载着千年智慧的竹简,都将化作青烟直上云霄。
而我,将站在火前,看着旧世界的灰烬落在新帝国的地基上,开出带刺的花。
4咸阳城外的焚书台形如倒扣的青铜鼎,九根蟠龙铁柱矗立如狱,铁柱之间用铁链串起万千竹简,在夜风里发出沙沙的轻响,像极了当年函谷关外六国使节递交降书时的窸窣声。
我站在台前,袖中《论语》的棱角硌着掌心,那是今早从淳于越书房暗格里取的,书页间还夹着片泛黄的橘叶,叶脉上隐约可见“克己复礼”的蝇头小楷。
“丞相,时辰到了。”
赵高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他今日穿了身朱红色的中官朝服,衣领上绣着狰狞的饕餮纹,与他脸上的笑意相得益彰。
我注意到他腰间挂着新得的玉蝉,雕工粗劣却刻意露在外面,那是昨夜某位想免于焚书的儒生送的。
淳于越被绑在中央铁柱上,白色的儒生长衫已被撕得破烂,露出瘦骨嶙峋的肩膀。
他的头发被血粘在铁柱上,干涸的血痂沿着脖颈流进衣领,像条丑陋的赤练蛇。
看见我走近,他突然剧烈挣扎,铁链撞击铁柱发出刺耳的声响:“李斯!
你看看这火!
看看这些竹简!”
我抬手示意,士兵们将火把抛向柴堆。
最先燃烧的是一堆《诗经》残卷,竹简上的朱砂评点在火中蜷曲成红色的虫,《关雎》的句子在青烟里碎成齑粉。
淳于越的脸被火光映得通红,他突然开始吟诵《春秋》,声音沙哑却清晰,每一个字都像火星溅在我心上。
“够了!”
我厉声喝止,却听见自己颤抖的声音。
火堆里爆出一声脆响,不知哪卷竹简里藏着的玉镇纸炸裂开来,碎玉片飞掠过淳于越面颊,划出细长的血痕。
他忽然笑了,血珠顺着笑纹流进嘴角:“李斯,你烧得掉竹简,烧得掉人心么?
我鲁国的孩童,就算在田里放牛,也能背出《论语》第三章!”
我转身走向监刑台,鞋底碾过一枚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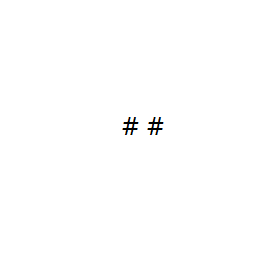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