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主角分别是江凝热门的其他类型小说《回家前,请确认父母未换脸后续》,由网络作家“左手烟蒂”所著,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本站纯净无弹窗,精彩内容欢迎阅读!小说详情介绍:自己高中时的房间。房间的陈设几乎没变。木头书桌上还贴着她贴的《格列佛游记》漫画,墙角还堆着一摞早年的课本,床头贴着她母亲那年写的手写纸条:“考研冲刺,家是你的港湾。”她曾经把它当安慰,如今读来只觉得讽刺。那张床太小,翻身都困难,她翻来覆去睡不着。凌晨两点,她起身去厕所,走廊昏黄的灯还亮着。走过厨房时,她听见父母卧室传来一段小声对话。“她明天会不会走?”“走什么走,工作又不是正经的,有她哥能挣钱吗?”“她这性格,别给脸不要脸。”她靠在墙后,听着心口像压了块铁。⸻第二天清晨,她照旧早起。刚打开手机,发现网络断了。她想连Wi-Fi,密码输入三遍都显示错误。“妈,家里换密码了?”“我哪知道密码啊,问你爸去。”她走到客厅问父亲。“断了。”父亲...
《回家前,请确认父母未换脸后续》精彩片段
自己高中时的房间。
房间的陈设几乎没变。
木头书桌上还贴着她贴的《格列佛游记》漫画,墙角还堆着一摞早年的课本,床头贴着她母亲那年写的手写纸条:“考研冲刺,家是你的港湾。”
她曾经把它当安慰,如今读来只觉得讽刺。
那张床太小,翻身都困难,她翻来覆去睡不着。
凌晨两点,她起身去厕所,走廊昏黄的灯还亮着。
走过厨房时,她听见父母卧室传来一段小声对话。
“她明天会不会走?”
“走什么走,工作又不是正经的,有她哥能挣钱吗?”
“她这性格,别给脸不要脸。”
她靠在墙后,听着心口像压了块铁。
⸻第二天清晨,她照旧早起。
刚打开手机,发现网络断了。
她想连Wi-Fi,密码输入三遍都显示错误。
“妈,家里换密码了?”
“我哪知道密码啊,问你爸去。”
她走到客厅问父亲。
“断了。”
父亲坐在沙发上喝茶,“你哥说现在节俭环保,就关了路由器。”
“那你们手机怎么上网?”
“我用的流量卡。”
父亲一边说,一边递给她一张报纸,“你看看,城东那边有工程招画画的,你不是学美术的吗?”
江凝没有接,只是点点头。
⸻她回房间,发现自己的银行卡竟然无法绑定支付,试图订车却因为验证短信失败而中止。
她坐在床沿,手机在手里却像一块冰。
她明白了:他们不是在等她回家,是早就准备好了要她“回笼”。
那不是一场偶然的呼唤,是早就布好的“困局”。
她起身去阳台透气,想打开窗子,却发现窗锁换了密码锁,滑轨也被钉死。
房间就像一个软封闭病房,干净整洁,无法逃离。
她忽然想起小时候养过的一只鸟。
那只鸟飞不起来,却一直被关在一个透明小笼子里。
母亲说:“它飞出去就会死,外面太冷。”
现在她才懂,原来那只鸟一直不是它飞不出去,而是——它从没真正拥有过飞走的钥匙。
⸻她回到书桌前,掀开抽屉,抽出一张旧图纸。
那是她高三时画的《逃离计划》——一张用素描笔画的小地图,上面标注着“市中心车站补课机构母亲不会找的地方”。
她那时候每晚都想:等我18岁,我就离开这里。
但现在,她28岁,回来了。
她低头,笑
还有一行被划掉的句子:“妈妈说,女孩子不能太自由,太自由会被人抢走。”
江凝盯着这行字,喉咙一紧。
那句话她依稀记得,是母亲在她十岁那年对她说的。
那年她第一次一个人跑到小镇东边的画室写生,回来后母亲大怒,骂她“不守妇道”,说如果哪天出事了就是“自找的”。
那年之后,她再也没一个人出过门,哪怕是去买水彩。
她一页页翻,发现整本日记到后期几乎全是空白。
那是一段“自我主动消失”的年纪。
她不再写,不再画,不再提意见,只做一个听话的、安静的、不惹事的孩子。
而母亲,却总在外人面前骄傲地说:“我家女儿最省心。”
她靠在椅背上,闭着眼,回忆像海水一样淹过来。
⸻她十八岁那年想报美术专业,母亲说:“考美术你想去北上广?
你要是敢报,我就一头撞死在这屋里。”
她把画夹烧了,复读一年,最后去了母亲选的师范学院,读了母亲选的中文系。
大学四年,她每年寒暑假都要回家陪床——母亲总会在她期末周突发病症,“胃出血心悸哮喘骨痛”,每次都在她有重大安排的时候。
而她,永远只有两个选择:回来,或者成为“没人性的女儿”。
她从没告诉过别人,她人生中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场画展,是在研究生第二年偷偷参加的——她用的是假名、假邮箱、画廊也从未知道她的身份。
那晚她站在展览馆角落,偷听别人议论她的作品时,差点哭出来。
不是因为骄傲,而是因为她终于成了自己。
可现在,她回来了,又一次被塞进了那个无形的框架。
她喘不过气来。
⸻她打开电脑,写下了一段话:“有一种家庭,是不需要锁链的。
它用爱和责任的名义,把你困在自己造的玻璃屋里。
你看似自由,实则连呼吸都带着他人的影子。”
她手指顿了顿,点了保存。
她已经开始计划,如何离开——彻底离开,不留一丝可以再被拖回的借口。
⸻第四章:你不能逃,因为我们说你不能江凝是在中午吃饭时,第一次感觉到“众口铄金”的重量。
那天的饭桌比以往更热闹。
两位亲戚前来探望母亲,一位是姑妈,另一位是舅舅。
桌上摆了七八个菜,荤素搭配,汤汤
第一章:接你回家,不是让你自由江凝到家的那天,是个晌午刚过、阳光阴毒的夏日。
她背着简单的行李包,手里拎着从高铁站买来的水果,走出出租车的时候,热气扑面而来。
空气潮得发黏,小区门口的红砖墙上一块块脱皮,像极了她小时候病了脱皮的手肘。
三年没回来,这里竟没什么变化。
还是那栋三层红砖自建房,斑驳的白漆铁门,门口贴着去年没撕干净的春联。
门前的猫窝着晒太阳,电线杆上还挂着她上初中时就存在的“疏通下水道”招贴广告,字体已经褪得看不清了。
江凝站在门前站了一会儿,才敲门。
很快,门被推开,是她父亲。
江父穿着一件洗得发灰的老头衫,神色平静到毫无波澜。
他看了她一眼,像是确认了包裹没寄错地址,点点头,转身进屋。
“你妈在床上呢,上午又说胸闷,喊你回来喊了两天。”
他边走边说。
江凝没作声。
她提着水果进门,鞋柜上还摆着她小时候的旧拖鞋,只是鞋底已经被踩得扁扁的,像是曾经的小孩也被时间压成了一团褶皱。
她脱鞋、洗手,动作机械。
厨房里飘着咸香味儿,是老家的咸鱼青菜。
她母亲喜欢的口味,她曾经最讨厌的气味。
客厅的沙发依旧摆着老式的竹席靠垫,茶几上的遥控器、塑料扇子、茶杯井井有条,仿佛岁月被封存在这一刻,从未走远。
她走进里屋,房门没关。
母亲躺在床上,头发整齐地别在枕边,穿着病号服,但妆还在——薄薄一层蜜粉、眉毛略描,看起来像是刚准备参加体面的小区“老年健康讲座”,而不是危在旦夕的重症病人。
“妈,我来了。”
江凝站在床边,轻声说。
母亲慢慢睁眼,目光里带着一瞬的冷静,然后才显出疲态:“来了啊……你总算还是愿意回来看看我这个妈。”
这句话,像锈刀划在瓷盘上,声音尖锐却低沉。
江凝把水果放在床头柜上,“你不是说要住院检查吗?
什么时候去医院?”
“哎呀,我都这样了,跑医院干嘛。”
母亲叹气,“家里有你在,我就安心多了。”
“医生不是说你有梗阻性病症?”
她继续追问。
“医生就是喜欢吓人。”
母亲摆摆手,声音慢悠悠,“我也不想拖累你……可现在你哥那
带记者去。
你知道杭州那边有媒体在跟进‘家庭身份剥夺’专题吧?
我有对接人。”
江权顿了一下,脸色难看:“有话好好说,别这么撕。”
“我已经说得很慢,很轻了。”
江凝微微一笑,“以前我一哭你们说我矫情,我一沉默你们说我阴沉,我一争辩你们说我不孝。
那现在,我不哭、不闹、不解释,就做事。”
“你们不是最怕我把家事拿出去说么?
那我就说,让他们看看你们想锁住的‘孝女’到底是个什么人。”
母亲拿着勺子手在抖:“你敢。”
江凝走到她跟前,低声道:“你不是怕我不孝,你是怕我成为一个你不再能定义的人。”
母亲猛地站起:“我病了你都不信!
你看看我身体!
你以为我真的是演戏?”
江凝后退一步,从口袋里拿出录音笔。
“这是你上周说的:‘我一病你就回来,我还真得保重点,别病太早了。
’”她按下播放。
录音中,母亲声音清晰而咬牙切齿。
餐桌陷入长久的沉默。
江权终于站起来:“……你想干嘛?”
“我不需要你们怎么做,我只是告诉你们,从现在起,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保护我自己。”
“我会起诉你对我名下财产的使用。
我会要求重新审定母亲的精神与行为状态,以便我能合法获得‘拒绝照顾权’。”
“我会将所有这几周的心理控制、信息封锁、身份侵占的记录,交给律师团队。”
“你们有你们的剧本,我也有我的清算。”
⸻当天,江凝去了派出所。
她没有举报母亲。
她知道,情绪操控无法量化。
但她启动了两项:• 对房产公证流程的行政复核申请;• 针对她身份证被冒用的民事举证通报。
接待她的警员问她:“你确定这不是家庭纠纷?”
她淡淡一笑:“家庭纠纷,是两个人都想解决;现在,是我一个人要逃生。”
⸻她搬出了家,在外租了一间小房子,暂居。
母亲多次来电未接,江权发过一次短信:“别太绝,亲情不能割。”
她回了一句:“你误会了,我不是割,是你们早割过我,现在我只是在缝。”
她开始整理文字,把这段经历写成系列短篇,投给一个专栏公众号《剥离者》。
她在第一篇里写道:“家不是控制的理由,父母也不是不讲证据的
有一份复印件和手机拍的照片。”
对方沉默了一会儿:“我建议你先跟他沟通,家务事走法律风险很高。
我们这边,暂时很难立案。”
江凝握着手机,心一点点沉下去。
她不是没想过对抗。
只是她知道,这种“家务化的剥夺”最难处理。
你没法证明对方“恶意”,你甚至没法证明你“不是自愿的”。
而你,只是因为太清醒,所以显得“不孝”。
⸻第二天一早,母亲再次“倒下”。
江凝起床后,发现母亲躺在地上,嘴唇发白,眼神空洞地望着天花板。
“妈?”
“我……我头好晕……可能是昨天太累了。”
她扶着母亲躺回床上,母亲喘得厉害,眼里却没有惊慌,反倒有种熟悉的“等待你反应”的平静。
“要去医院吗?”
“不用了。”
母亲虚弱地说,“你在这儿就行了。”
“还是我陪你去看看吧。”
“不用了……只要你不走,我就不难受。”
那句话像一根细针,刺进江凝的神经。
她站在床边,头皮发麻,突然觉得这一切是个闭环——她无法说服他人,也无法逃脱。
她曾试图改变系统,系统却只是关上了窗,继续运行。
⸻傍晚时分,门铃响了,是邻居老太太送汤来。
“你妈最近真是辛苦啊,我听她说你终于想开了,愿意回来定居了,真是孝顺。”
“我没有。”
江凝淡淡回道。
老太太愣了愣:“不是你妈说的吗?
她都让你把杭州那边房子退了。”
江凝面色一变。
她转身冲进屋里,打开抽屉,找出她的户口簿和身份证——身份证还在,但户口簿上她的居住地址被涂改过。
她的房子在父母的口中,已经“被处理”。
她打开手机App,发现自己名下银行的一张卡于上周被使用——支付对象是一家小型地产中介公司。
她打电话过去,客服说:“那是我们代办产权公证的收款。”
她瞳孔一缩。
不是猜测了。
是开始了。
⸻夜里,她坐在书桌前,把这些碎片信息一条条记下:• 母亲反复装病,制造情绪控制;• 哥哥使用她身份签字,或已涉侵权;• 父亲默认沉默,退场但构成包庇;• 亲戚统一口径,社会评价系统化施压;• 她尝试对外求助,但无证据难推进。
她写完最后一句:“我曾经以为逃跑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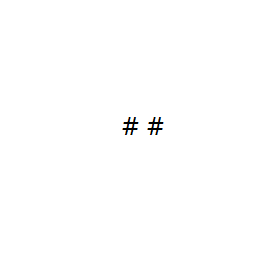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