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主角分别是小陈热门的其他类型小说《唐瓷年代小陈热门无删减全文》,由网络作家“房三善”所著,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本站纯净无弹窗,精彩内容欢迎阅读!小说详情介绍:。我这灶火一日三顿为你们开,煤球钱便要贴进去半袋。”旁边择菜的黄阿姨突然插话:“小伙子莫听他哭穷,去年给工商局开伙,每人一元二角呢。”暮色漫进厨房时,曾师傅忽然从裤兜摸出张皱巴巴的成绩单,儿子的数学卷子上写着九十九分:“下月开学要交三十元杂费——得,就九毛,算我给你们几个光棍接风。”他说话时避开我的目光,盯着窗外摇晃的竹帘,那里晾着几件补丁摞补丁的校服。当晚,四个光棍在宿舍以搪瓷缸碰杯,泡着从家中带来的霉豆腐。老张从帆布包摸出半瓶米酒,言说是在查扣的走私货物里“顺”的——后来才知,是他自掏腰包在副食店买的,瓶身标签还是用糨糊重新贴的。月光从破了角的窗帘漏进来,照见我们映在墙上的影子,比饭盆里的肉片还要单薄几分。次日清晨,谢师傅在食堂...
《唐瓷年代小陈热门无删减全文》精彩片段
。
我这灶火一日三顿为你们开,煤球钱便要贴进去半袋。”
旁边择菜的黄阿姨突然插话:“小伙子莫听他哭穷,去年给工商局开伙,每人一元二角呢。”
暮色漫进厨房时,曾师傅忽然从裤兜摸出张皱巴巴的成绩单,儿子的数学卷子上写着九十九分:“下月开学要交三十元杂费——得,就九毛,算我给你们几个光棍接风。”
他说话时避开我的目光,盯着窗外摇晃的竹帘,那里晾着几件补丁摞补丁的校服。
当晚,四个光棍在宿舍以搪瓷缸碰杯,泡着从家中带来的霉豆腐。
老张从帆布包摸出半瓶米酒,言说是在查扣的走私货物里“顺”的——后来才知,是他自掏腰包在副食店买的,瓶身标签还是用糨糊重新贴的。
月光从破了角的窗帘漏进来,照见我们映在墙上的影子,比饭盆里的肉片还要单薄几分。
次日清晨,谢师傅在食堂门口贴出一张手写告示,字迹歪歪扭扭:“单身职工餐,每餐九毛,凭票打饭。”
所谓饭票,是黄阿姨用废旧卷宗纸裁的,每张都盖着曾师傅的搪瓷缸底印——蘸了红墨水,倒像是落了几滴血。
我头回正式在食堂打饭,谢师傅特意多舀了半勺青菜汤,油花在汤面晃了晃,终究沉了底。
他压低声音道:“省着些用,你们张哥昨夜已垫了饭钱——他那点薪水,还要给老家的老娘买药。”
八月将尽,梅城突降暴雨。
雨水从食堂青瓦缝漏下,在地上砸出铜钱大的坑。
我们蹲在灶台边接水,谢师傅忽然指着窗外的泡桐树:“待你们搬新宿舍时,这树便要开花了。”
他说话时,黄阿姨正将霉豆腐拌入我们的菜中,酸香混着雨气,竟成了这个夏天最难忘的滋味。
月底寄钱,我在邮局窗口踌躇良久。
汇款单上的“一百元”墨迹未干,口袋里剩下的十元纸币被体温焐得发软。
路过副食店,买了包最便宜的“珠江桥”牌味精——曾师傅的汤锅里,已许久未飘出肉香了。
回到宿舍,老张正在用报纸包晒干的咸鱼,说是给曾师傅捎的:“他儿子爱吃这个。”
窗外雨仍在下,打在晾着的的确良衬衫上,发出细碎的声响。
我摸着床头母亲塞的咸萝卜干,忽然觉得,这个满是煤烟味与欢笑声的食堂,正渐渐
香混着桂树苗的土腥味,在深秋的风里漫开。
月底对账,谢师傅的算盘珠子打得山响:“你们四个这个月共百又八勾,合计九十七块二毛。”
他特意抹去零头,记成九十五元整,“剩下的便当作桂树苗的肥料钱罢。”
其实我们都晓得,他偷偷将自己的加班补贴填进了账本。
那日傍晚,我们在宿舍煮了锅白菜豆腐汤,叫上谢师傅和黄阿姨同饮。
老张摸出从老家带来的红薯酒,谢师傅抿了一口,眼眶便红了:“跟我爹酿的一个味。”
月光从晾着的白大褂间漏下,照见他腕上的疤痕在酒气里发亮——那是岁月刻下的印记,亦是温暖的注脚。
当第一片银杏叶落在食堂窗台,我们终于懂得,与谢师傅的“较量”原是心照不宣的互助:他以食堂的烟火温暖四个异乡人,我们以年轻的活力为他的生活添些光亮。
正如他常说的:“饭桌上不分上下,吃饱了才有精力去审犯人。”
第三章 饭盆里的江湖深秋的梅城是被揉碎的金箔,香樟叶扑在食堂青瓦上,簌簌地响,像是谁在悄悄数着饭票。
每日正午十二时,搪瓷盆相击的叮当声便在走廊炸开,四个光棍踩着下班铃往食堂跑,鞋底在水磨石地面擦出刺啦刺啦的响——并非饿极,是要赶在谢师傅分菜前占个好位置,瞧那架势,倒像是去赴一场无声的战役。
谢师傅的分菜台是块磨得发亮的榆木案板,搪瓷盆一字排开,青菜叶上码着的肉片,三肥两瘦,每盘不多不少五块,倒像是用尺子量过的。
老张总爱将盆沿磕在窗口:“谢师傅,今儿的肉片怎的比小李的薄?”
嘴上这么说,眼睛却盯着盆底——他晓得谢师傅定会用铁勺多拨块带筋的,“年轻人少吃些肥的,省得跑不动抓不住走私犯。”
谢师傅嘴上应着,手却偏将最嫩的里脊肉舀给总跑外勤的小李,自己只留带皮的边角料,烩白菜时连油花都要多搅两圈。
最紧张的是汤盆见底的时候。
黄阿姨熬的海带汤,第三勺后便见了汤渣,我们便成了“打捞队员”,汤勺在盆底搅出漩涡,海带丝缠着豆腐块往勺心跑。
有次小李喝汤喝出了响,谢师傅突然从灶台后探出头:“慢些喝,锅里留着‘干货’呢。”
原来是他早将招待
个勾——美其名曰“体力补偿”。
最妙的是老张,总将饭票撕成两半,说“一顿吃半勾,省钱娶媳妇”,谢师傅却假装没看见,照样给足分量:“傻小子,吃饱了才有力气攒钱。”
十一月的梅城飘起冷雨,食堂后窗的小花坛蔫了大半,谢师傅却在墙角摆了个破搪瓷盆,里面泡着发了芽的土豆:“留着炒土豆丝,比青菜经吃。”
我们知道,他儿子的学费还差二十块,正变着法儿省伙食费。
于是次日,小李从码头带回半筐别人不要的小鱼,老张翻出压箱底的五香粉,我将母亲寄来的干辣椒全倒进厨房——那顿香煎小鱼配辣椒,辣得人眼眶发热,谢师傅却红了眼:“比国营饭店的大厨做得还香。”
饭盆里的江湖没有刀光剑影,有的是谢师傅抖勺时的“偏心”,黄阿姨藏在菜里的半勺猪油,还有我们故意多画的饭勾。
当第一片雪花落在食堂窗台,谢师傅开始盘算买煤球,我们则在宿舍偷偷攒粮票——不为别的,就为让这个装满烟火气的小江湖,在寒冬里多飘些暖意。
某个起雾的早晨,我见谢师傅蹲在桂花树旁,用旧搪瓷缸给树苗浇水。
他腕上的疤痕在晨雾里若隐若现,像条沉睡的鱼。
黄阿姨说,那是他去年救实习生时留下的,可他自己总说:“没啥,比锅里的油点子疼不到哪儿去。”
话音未落,老张的搪瓷盆已磕在窗口:“谢师傅,今儿的肉片该多两块罢?
我昨晚帮您劈了三捆柴呢!”
笑声惊飞了树上的麻雀,饭盆里的肉片在晨光中泛着油光。
这江湖,原不是刀光剑影的江湖,而是藏在半勺猪油里的江湖,是浸在甜酒蛋香里的江湖,是几个光棍与一位师傅,在煤烟与饭香里,彼此温暖的江湖。
正如谢师傅常说的:“饭吃得香不香,不在于盆里有几块肉,而在于跟你抢肉吃的人,是不是把你当自家人。”
第四章 冬天的电饭煲一九九二年的冬是个狠角色,梅城刚进腊月便飘起冻雨,食堂青瓦上结的冰棱,将谢师傅的蓝布围裙都冻出了硬边。
他蹲在灶台前拨拉煤球,火星子溅在腕上的烫疤上:“老家捎信说,老爹的风湿腿又犯了,得回去一趟。”
说时不敢看我们,火钳将煤块戳得噼啪响——我们都
知道,他是放心不下四个光棍的肚皮。
停伙前一日,谢师傅打开食堂储物柜,里面半袋米、三根蒜苗、半罐猪油码得齐整:“省着吃,黄阿姨明日也歇班。”
又塞给我一张纸条,铅笔歪扭画着电饭煲煮菜图:“腊肉要先蒸,蒜苗炒到半焦再下饭……”末了摸出个塑料袋,里面是晒干的橘子皮:“煮汤时放两块,去腥味。”
那纸条边角卷着,像是被他反复揉过又展平的。
谢师傅走后,食堂铁门挂了锈锁,像道结了痂的伤。
头日中午,我在宿舍门口生煤炉,表哥送的旧电饭煲蹲在小马扎上,锅底还留着去年熬粥的黑印。
蒜苗在菜板上切得咔咔响,腊肉是母亲秋天寄的,藏在枕头下用报纸裹着,切开时油花顺着刀缝往下滴,倒像是时光在流泪。
小陈端着空碗从对门晃来,鼻尖冻得通红:“给点汤呗,我煮的白粥能照见人影。”
他碗里的粥稀得能映出窗外的屋檐,倒衬得我锅里的蒜苗炒腊肉格外奢侈——其实就几片肉,在青蒜里打转转。
正分着,小李推门进来,怀里抱着半只腊鸭:“车上老大送的,说抵饭钱。”
那腊鸭冻得硬邦邦,却让屋里添了些活气。
那只电饭煲成了我们的“灶王爷”。
煤炉太小,锅底总糊,我们便轮流守着:老张切菜,将冻硬的白菜帮子片得薄如蝉翼;小李在走廊尽头洗腊鸭,冰水将手指冻得通红;我盯着电饭煲,看米粒在沸水里翻跟头,恍惚间竟想起老家的土灶。
有次水放多了,米饭成了粥,老张灵机一动,掰进腊鸭骨头,撒把盐和胡椒粉,竟熬出乳白的浓汤,香气顺着门缝往外跑,引得来二楼的王科长探头:“你们这儿搞流水席呢?”
还摸出瓶豆瓣酱,说是爱人腌的。
最艰难是谢师傅迟归的那周。
天气预报说有冻雨,我们囤的米缸见了底,蒜苗早蔫成草绳,只剩几根皱巴巴的芹菜。
小李翻出压箱底的方便面,三包调料掰成四份,老张将搪瓷盆洗了又洗:“煮‘豪华版汤面’。”
正发愁,小陈举着塑料袋冲进来:“我表哥捎的红薯,烤着吃!”
走廊尽头的煤炉成了烤炉,红薯埋进热灰里,甜香慢慢渗出来,小李剥了皮分给大家,热气在他睫毛上凝成水珠:“小时候家里
只留带皮的边角料。
<真正的较量藏在细微处。
每逢周三“改善日”,谢师傅会在菜盆里埋几块炸鱼块,却故意手抖让鱼块滑回盆底——直到我们学会用搪瓷盆轻磕窗口,他才笑着多舀一勺。
黄阿姨则趁谢师傅熬汤时,往我们碗里多撒把虾皮,末了叮嘱:“莫要告诉老谢,只说汤里的‘固体’自己长了脚。”
那个秋雨绵绵的傍晚,小李出差归来得晚,食堂早已关门。
我们正欲泡方便面,谢师傅却推门进来,怀里抱着个用毛巾裹得严实的搪瓷盆:“热乎的豆角焖面,你黄阿姨特意留的。”
掀开盖子,蒸汽混着肉香扑面而来,面条底下竟藏着两块完整的红烧肉——那是招待所用剩的边角料,他偷偷攒了三日。
发薪日成了食堂的“节候”。
每月初九,我们将饭票钱凑齐,用信封装了塞进谢师傅的白大褂口袋。
他总推搡着:“不急,等月底一并算罢。”
可我们知道,他抽屉里压着儿子的学费单,截止日就在每月十五。
有次老张多塞了五元,说是“提前预支改善费”,谢师傅却红了脸:“使不得,你们年轻人还要攒钱讨媳妇。”
十月底忽生变故,陈胖子宣布招待所要扩招临时工,食堂场地须得缩减一半。
谢师傅蹲在灶台前抽了半宿烟,烟头在黑暗里明灭如萤火。
次日,我们见食堂的桌子挪到了走廊,蓝白格子桌布换作旧报纸,谢师傅的菜盆却依旧摆得齐整,每盘肉片底下藏着焯过水的豆芽:“这样看着多些。”
他挠着头,像是做错事的孩童。
作为回礼,我们帮谢师傅干起杂活。
老张用废木料搭了防风棚,小李从码头带回半袋海盐,我将母亲寄来的豆腐乳分了半罐给黄阿姨。
一日,谢师傅的儿子来送伞,我们见那孩子穿着打补丁的校服,却捧着全班第一的数学卷子——方知谢师傅每日多给我们的半勺猪油,原是从自家炒菜锅里省出来的。
天气转凉,谢师傅在食堂门口种了棵桂花树。
他说:“等开花了,摘来腌糖桂花,煮粥甜得很。”
我们蹲在旁边培土,黄阿姨忽然道:“老谢年轻时可是国营饭店的大厨,为了照顾生病的老娘才来此处。”
话音未落,谢师傅已端出刚出锅的辣椒炒肉,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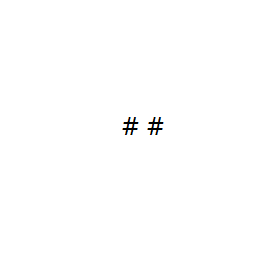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