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主角分别是文昭卢远的其他类型小说《愿为江水,与君重逢文昭卢远无删减全文》,由网络作家“火云邪神拖鞋版”所著,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本站纯净无弹窗,精彩内容欢迎阅读!小说详情介绍:1江州城外,清溪边,夏日炎炎。知府衙门新发的告示,歪歪扭扭贴在石碑上,字迹模糊。百姓们围着,看不懂,只是焦急地嗡嗡着。城里一桩命案,扯上了富商贾家,百姓们都怕,怕这案子又被压下。文昭那时,不过是衙门里一名小书吏。他笔墨精熟,心思却不如笔尖那般活络。他习惯了沉默,只把世事看在眼里。人群中,一人挤了进来。他身着青衫,不是官服,却自带一股凌厉气势。他扫了眼告示,眉头拧成个疙瘩。“这写得什么?”他问,声音洪亮,带着一股子不平气。旁人摇头。那人哼了一声,大步走到碑前。他抬手,指着告示,口齿清晰,将案情始末,其中贾家的勾当,一一念了出来。百姓们听了,先是安静,接着便炸开了锅。义愤填膺者有之,拍手称快者有之。文昭站在角落,看着那人。他高大,身板挺...
《愿为江水,与君重逢文昭卢远无删减全文》精彩片段
1江州城外,清溪边,夏日炎炎。
知府衙门新发的告示,歪歪扭扭贴在石碑上,字迹模糊。
百姓们围着,看不懂,只是焦急地嗡嗡着。
城里一桩命案,扯上了富商贾家,百姓们都怕,怕这案子又被压下。
文昭那时,不过是衙门里一名小书吏。
他笔墨精熟,心思却不如笔尖那般活络。
他习惯了沉默,只把世事看在眼里。
人群中,一人挤了进来。
他身着青衫,不是官服,却自带一股凌厉气势。
他扫了眼告示,眉头拧成个疙瘩。
“这写得什么?”
他问,声音洪亮,带着一股子不平气。
旁人摇头。
那人哼了一声,大步走到碑前。
他抬手,指着告示,口齿清晰,将案情始末,其中贾家的勾当,一一念了出来。
百姓们听了,先是安静,接着便炸开了锅。
义愤填膺者有之,拍手称快者有之。
文昭站在角落,看着那人。
他高大,身板挺直,眉宇间一股正气。
阳光洒在他肩头,像镀了一层金。
他感觉,这人不同。
后来文昭才知,他叫卢远。
不是本地人,早年考中过举人,却不入仕途。
他游历四方,专替百姓申冤,人称“卢青天”。
这次恰好路过江州,听闻此事,便插手了。
贾家在江州势力盘根错节。
卢远一介入,便引来了麻烦。
他住的客栈,每日都有人上门威胁,或是直接送来银票。
卢远从不收,当面撕碎,扔出门外。
文昭心里佩服。
他想,世上真有这样的人。
一日傍晚,文昭独自在衙门里整理卷宗。
烛火摇曳,照得人影幢幢。
卢远推门而入,一身风尘,带着酒气。
“文书,忙着?”
卢远的声音带着笑意。
文昭抬头,点头。
卢远坐下,从怀里掏出几张纸,推到文昭面前。
“我写了几份状纸,给贾家罗列了罪状。
你瞧瞧,还有无错漏?”
文昭接过。
卢远笔力遒劲,字里行间透着股凛然正气。
文昭细看,发现几处措辞,稍作修改,更添几分严谨。
“如此,可呈报巡按大人。”
文昭说。
卢远拍桌:“好!”
他看向文昭,眼神里多了几分欣赏,“你这人,看着闷,心里却亮堂。”
文昭不语,只是嘴角微扬。
那天起,两人便常在一起。
卢远每日在江州城里奔走,找证人,收集证据。
文昭则在衙门里,替他打点关节,
核对卷宗,有时甚至帮他拟写公文。
卢远性子急,有时冲动。
他想,直接去贾家大闹一场,看他们还敢嚣张?
文昭听了,摇摇头。
“卢兄,贾家势大,硬碰硬,恐有闪失。”
“那你说怎么办?”
卢远问。
“先将证据坐实,再上报巡按大人。
贾家再大,也大不过朝廷律法。”
文昭说。
他声音不高,却有股定力。
卢远听了,沉思半晌,点头:“你说的对,是我急躁了。”
他们二人,一动一静,一明一暗,配合得天衣无缝。
为了贾家案,他们常常秉烛夜谈。
有时在卢远的客栈,有时在文昭简陋的住处。
他们就着一壶清茶,几碟小菜,聊案情,也聊天下事。
“这天下,苦百姓久矣。”
卢远叹息,语气低沉。
“是啊。”
文昭应和。
他知道卢远的心。
“若能让这天下,少些不公,少些疾苦,便是粉身碎骨,也值得!”
卢远眼中闪着光。
文昭看着他,心里一股热流涌过。
他想,他愿助卢远一臂之力。
卢远不善应酬,有时得罪了人,文昭便悄悄替他弥补。
卢远不拘小节,有时言辞过激,文昭便在私下提醒。
卢远是火,文昭是水。
水浇在火上,不是熄灭,而是让火烧得更旺,更持久。
贾家案最终告破。
巡按大人介入,贾家倒了,贾老爷被判斩首示众。
江州百姓无不拍手称快,称卢远为“卢青天”。
卢远名声大噪。
许多地方的百姓听闻他的事迹,纷纷上门求助。
卢远来者不拒,带着一身正气,继续他的江湖生涯。
临别时,卢远特意来找文昭。
“文书,此番多亏有你。”
卢远拱手,神色郑重。
文昭摆摆手,没有居功。
“卢兄此去,定能名扬天下。”
卢远笑:“天下何其大,我只求心安。”
他顿了顿,“你可愿随我一道?”
文昭心头一震。
他看着卢远的眼睛,那里面有火焰,有光。
“我愿随卢兄,匡扶正义。”
文昭说,语气平静,却字字千钧。
卢远大笑,拍了拍文昭的肩。
“好!
好啊!
文昭,你我兄弟,此生不负!”
那一刻,清溪潺潺,阳光正好。
文昭觉得,他找到了一条路,也找到了一份,值得追随的光。
他不知道这条路会通向何方,但他知道,只要卢远在,他便不会迷失。
他随卢远离开了江州,离开了那间
小小的衙门。
从此,他不再是默默无闻的书吏,他成了卢远身边,那个最值得信赖的影子。
2卢远带着文昭,一路北上,直抵京城。
卢远的名声,早已传到朝堂。
当今圣上,初登大宝,正欲革新朝政,清除弊端。
卢远这样有胆识、有正气的江湖人士,正是他所需要的。
卢远被召入宫,面见圣上。
他直言不讳,陈述百姓疾苦,直指朝政积弊。
圣上听了,龙颜大悦,当即便封他为大理寺少卿。
文昭随卢远一道入京。
他没有得到官职,只是以卢远幕僚的身份,住在卢府。
“你何不也求个官职?”
卢远问他。
文昭摇头:“我愿在卢兄身后,替你分忧。”
卢远听了,心里暖和。
他知道,文昭是真心实意,不图名利。
大理寺少卿,掌管刑狱,职责重大。
卢远上任后,雷厉风行,处理了一批积压的冤案,惩治了一批贪官污吏。
京城上下,一片震动。
可树大招风。
卢远的举动,很快便触犯了朝中权贵的利益。
那些老臣,世家大族,开始联合起来,对他百般阻挠。
“卢少卿,你这般激进,恐伤及朝局稳定啊。”
有老臣阴阳怪气地说。
卢远拍案:“朝局不稳,正是因这些贪官污吏横行!
不除之,何谈稳定?”
文昭在旁,看着卢远与那些老臣周旋。
他知道,卢远心里苦。
他想做实事,可阻力重重。
每日散朝后,卢远回到府中,常是满身疲惫。
他会坐在书房里,一言不发。
文昭便默默地给他泡茶,研墨。
他看着卢远的背影,心疼。
“卢兄,今日朝堂上,那王大人所言,看似在理,实则暗藏杀机。”
文昭说。
卢远回头看他:“哦?
你如何看?”
文昭细细分析:“王大人提议,将流民安置一事交由地方乡绅自理。
此举看似减轻朝廷负担,实则给了地方豪强侵占土地、鱼肉百姓的机会。”
卢远猛地起身,在书房里踱步。
“是啊,是我一时未察。
这些老狐狸,嘴里都是仁义道德,心里全是龌龊算计!”
“卢兄,日后言行,需更加谨慎。”
文昭提醒。
“我知道。”
卢远叹气,“可这京城里,步步都是陷阱。”
文昭点头:“我们需更加小心。”
从此,卢远在朝堂上,多了一分稳重。
他的奏章,他的言辞,在文昭的润色下,既
保持了卢远的锋芒,又多了几分滴水不漏。
卢远渐渐意识到,文昭是他不可或缺的左右手。
他有什么想法,都会先与文昭商议。
文昭的冷静和远见,总能弥补他的冲动和不足。
圣上对卢远日益器重,欲提拔他为宰相。
消息传出,朝野震动。
那些老臣更是坐不住了。
他们开始散布谣言,说卢远结党营私,说他沽名钓誉,甚至派人到卢府外,暗中监视。
有天,文昭从外面回来,脸色铁青。
“卢兄,我听说,有人在暗中调查你的过往。”
文昭说。
卢远眉头紧锁:“查什么?
我这一生,光明磊落!”
“他们查你在地方上处理的那些案子,想从中找出破绽。”
文昭说,“甚至,他们还盯上了你的家人。”
卢远猛地站起来,拳头握得死紧。
“这些人,竟敢如此!”
他语气冰冷。
“卢兄,你我需商议对策。”
文昭冷静地说。
他们二人连夜商议。
文昭建议卢远,暂时放缓改革步伐,避其锋芒。
“我不能退!”
卢远斩钉截铁,“一旦退了,便是向他们低头!”
文昭知道卢远的脾气,劝不住他。
然而,更大的风暴,终究还是来了。
一次,卢远在朝堂上,揭露了某位亲王暗中侵吞国有土地的罪行。
证据确凿,亲王被革去封号,贬为庶民。
这下,彻底捅了马蜂窝。
亲王背后,是当朝太后。
太后震怒,下旨彻查卢远。
彻查,便是罗织罪名。
卢远的亲信被抓,家眷被盘查。
甚至连文昭,也被人带走审问。
文昭在狱中,受尽折磨。
可他咬紧牙关,一个字也不肯透露卢远任何不实的信息。
他知道,这是卢远最后的防线。
卢远被罢免官职,抄家。
他被软禁在京郊一处偏僻的宅院。
文昭被放出来时,已是遍体鳞伤。
他顾不上自己,立刻冲到卢远的宅院。
宅院外,守卫森严。
文昭乔装打扮,贿赂了守卫,才得以进去。
卢远坐在院子里,白发又多了几缕。
他看着文昭,眼中闪过一丝心疼。
“文昭,你受苦了。”
卢远声音沙哑。
文昭摇头:“卢兄,他们查不到什么,你清白无辜!”
卢远惨笑一声:“清白又如何?
他们要的,不过是我的死。”
他指了指天。
“他们怕我。
怕我继续替百姓说话。
怕我动了他们的根基。”
文昭心如刀绞。
他知道卢远是好官,是好人。
可这世道,好人难做。
“卢兄,我们总能找到办法。”
文昭握住卢远的手,冰凉。
“办法?”
卢远眼中闪过一丝绝望,“他们连你都查,连我的家人都威胁。
他们要的,是彻底摧毁我。”
那夜,他们聊了很久。
卢远说起他年少时的梦想,说起他如何游历四方,说起他如何决心入仕为百姓做主。
文昭听着,心里沉重。
他知道,卢远不惧生死,但他怕连累家人,怕自己一世清名,最终被污蔑。
“文昭,我此生,无憾。”
卢远说,语气平静,像在说一件与他无关的事。
文昭看着他,心里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卢兄,你说什么?”
文昭的声音颤抖。
卢远只是笑笑,没有回答。
天亮时,文昭被守卫催促着离开。
他一步三回头,总觉得卢远的眼神,带着一种诀别。
他想闯进去,可那些守卫将他拦下。
他回到自己的住处,心里焦躁不安。
他总觉得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他坐不住,又回到卢远宅院外。
他想,他必须守着卢远,不能让他出事。
可他终究,还是晚了一步。
3那天是个阴天,天空灰蒙蒙的,像一块巨大的幕布,压在京城之上。
雨丝细密,打在青石板路上,湿漉漉的。
文昭站在卢远宅院外,心口像是压了块石头。
他昨夜辗转反侧,总觉得不安。
他想,今日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进去。
忽然,宅院里传来一阵骚动。
守卫们惊慌失措地奔跑着,嘴里喊着什么。
文昭心里一紧,顾不得许多,直接冲向大门。
“出什么事了?”
他抓住一个冲出来的守卫,厉声问。
守卫脸色惨白,结结巴巴地说:“卢……卢大人……他……他投江了!”
文昭的脑子“轰”地一声,一片空白。
他只觉得脚下发软,世界都开始天旋地转。
“不可能!
不可能!”
他嘴里喃喃着,一把推开守卫,冲进宅院。
他跑向后院,那里有一条小径,通往京城外那条蜿蜒的沁水河。
卢远常常去那里散步,说那里的水声能让人心静。
雨越下越大,打在他脸上,冰冷刺骨。
他冲到河边,河水湍急,卷着落叶和泥沙,呜咽着向前奔流。
河边围满了人,有官兵,有卢府的下人,还有一些闻讯赶来的百姓。
他们脸上,都带着惊
恐和悲伤。
文昭看到卢远的家人,卢夫人抱着孩子,哭得撕心裂肺。
卢远的仆从,跪在地上,哭得泣不成声。
文昭呆呆地站在那里,浑身冰冷。
他环顾四周,寻找着卢远的痕迹。
河边,一块青石上,放着一件被雨水打湿的衣衫。
是卢远的。
还有一封书信,压在衣衫下。
文昭冲过去,拿起那封信。
他的手颤抖着,展开信纸。
信上是卢远的笔迹,清晰而决绝。
“昭弟吾友,我知你心意。
然此身已污,不愿再累及家人,不愿再为奸人所趁。
我之清白,唯以死证。
吾所求,非个人功名,乃天下苍生。
此生未竟之志,望昭弟代为承之。
我愿为江水,洗尽此身尘埃,若有来世,与君重逢,再谋天下太平。”
信的最后,落款是“卢远绝笔”。
文昭看着信,泪水模糊了视线。
他想哭,可喉咙像被堵住,发不出一丝声音。
他的心,像被生生撕开一个口子,血淋淋的。
卢远,他真的走了。
用这样决绝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切。
是为了证明清白?
是为了保护家人?
还是因为,对这混浊的世道,彻底绝望?
文昭不知道。
他只知道,他的世界,塌了。
那个带领他,给他信念的卢远,没了。
河水哗哗地流着,像在哭泣。
文昭蹲下身,伸出手,想去触碰那冰冷的河水。
他想,卢远的身体,是不是就在这水里,随着江水,流向远方?
官兵开始打捞,百姓们也纷纷赶来,自发地帮助。
可卢远的身影,却再也没有出现。
他像一滴水,融进了浩瀚的江水里。
卢远投江的消息,很快传遍京城。
朝野震动。
那些攻击卢远的人,也都安静了下来。
他们达到了目的,却没人敢再多言。
太后下旨,将卢远的家人流放千里。
卢府被查抄,卢远的亲信,不是被流放,就是被贬官。
文昭在卢远的葬礼上,默默地站在一旁。
他看着卢远的牌位,那上面写着“卢远之墓”。
他想,卢远是入土为安了,可他留下的那些志向,那些未竟的事业,又该如何?
他感觉自己像个孤魂野鬼。
他想,他是不是也该跟着卢远去?
可卢远的信,那句“望昭弟代为承之”,像一把烙铁,烙在他的心上。
他知道,卢远将他的信念,他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自己身上。
他不能
辜负卢远。
他强撑着处理卢远的后事。
他将卢远的信,小心翼翼地收好。
那是卢远留给他最后的遗言,也是他此生,最重的使命。
卢远去世后,文昭离开了京城。
他没有回江州,也没有再入仕。
他找了一处偏远的山村,靠着帮人写信、教书为生。
他每日都会去村外的河边。
他会坐在河边,看着河水奔流不息。
他想,卢远就是这江水,永远向前,永不停歇。
他常常想起卢远的话,想起他们秉烛夜谈的夜晚。
他想,卢远为了百姓,为了社稷,付出了生命。
而他,还活着,还背负着卢远的遗志。
他知道,他不能就此沉沦。
他要活下去,活出卢远期望的样子。
他要替卢远,完成那些未竟的梦想。
可是,该怎么做?
他在这山村里,一待就是三年。
三年里,他白了头,瘦了身。
可他的眼神,却变得越来越清亮。
他读遍了卢远留下的所有书籍,整理了卢远的所有手稿。
他明白了卢远那些改革的深意,也明白了卢远那些超前的思想。
他意识到,卢远不是败了,他只是走得太快,超前了时代。
而他,文昭,必须将卢远的理念,用更温和、更持久的方式,一点点地,实现。
他看着河水,忽然明白了。
卢远化作了江水,而他,便是那江水中的一滴。
他要随着江水,继续向前,最终汇入大海,让卢远的理想,流淌到更远的地方。
4三年后,朝廷政局变动。
圣上日益年迈,太子监国。
新太子性情温和,也知前朝弊病,有意整饬。
文昭听闻这些消息,心里有了触动。
他想,这是个机会。
他没有贸然行动。
他先是暗中联络了一些卢远的旧部,那些因卢远被贬,但心怀抱负的官员。
他们散落在各地,等待着时机。
文昭写信给他们,字里行间,都透着一股坚定。
他将卢远的遗志,将他所思所想,一一告知。
那些旧部读了信,纷纷响应。
他们知道文昭是卢远最信任的人,也知道文昭的为人。
文昭决定,走出山村。
他先是到一个小县城,重新考取了功名。
他不再隐藏自己的才华。
他要让世人看到,他文昭,回来了。
他考中了进士,被授予了一份清闲的官职。
他没有急于求成,而是耐心等待。
他观察朝局,分析利弊。
他用卢远教
给他的智慧,审时度势,步步为营。
他先从小事做起,处理地方政务,为百姓排忧解难。
他做事认真,公正廉明,很快便得到了百姓的认可。
他的名声,一点点地传开。
太子听闻他的事迹,召他入京面圣。
文昭再次踏入京城,已是物是人非。
街道依旧繁华,可他眼里,却少了那份生机。
他想起卢远在这里的日日夜夜,想起他们为百姓奔走的时光。
他进宫面圣。
太子看着他,眼神中带着审视。
“文大人,你与先前的卢远卢少卿,交情匪浅啊。”
太子语气平淡。
文昭抬头,目光清澈,没有丝毫躲闪。
“殿下,卢大人乃天下少有的忠臣。
他心系百姓,为国为民,只是……不为奸佞所容。”
文昭说,语气平静,却字字铿锵。
太子盯着他看了许久,忽然笑了一下。
“文大人倒是个直性子。
不过,孤欣赏你这般直率。”
他问文昭:“你对朝政,有何看法?”
文昭没有急于表态,他只是缓缓道来,将卢远那些未竟的改革思想,用更婉转、更符合当下实际的方式,一一阐述。
他提出了新的土地政策,新的赋税制度,以及如何安置流民,如何遏制地方豪强。
太子听了,频频点头。
他发现,文昭所言,并非纸上谈兵,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切实可行。
“文大人,你可愿入朝为官,助孤一臂之力?”
太子问。
<文昭跪下,伏地叩首。
“臣,愿为殿下效犬马之劳,为天下苍生谋福。”
他心里清楚,他不是为太子效力,他是为卢远,为卢远未竟的理想而战。
文昭入了朝,从地方官做起,一步步升迁。
他先是从底层做起,深入民间,了解百姓疾苦。
他推行卢远生前未能实施的政策,润物细无声。
他不再像卢远那样锋芒毕露,而是以柔克刚。
他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分化那些顽固的旧势力。
他用三年时间,巩固了自己在朝中的地位。
他用五年时间,让卢远生前勾画的蓝图,开始有了雏形。
每当夜深人静,他会在书房里,点一盏孤灯。
他会拿出那封泛黄的信,反复阅读。
“我愿为江水,洗尽此身尘埃,若有来世,与君重逢,再谋天下太平。”
他常想,卢远啊卢远,你可看到了?
你未竟的理想,我正在替你
一步步实现。
你化作了江水,而我,是那江水中唯一的鱼。
我逆流而上,只为追寻你的足迹。
他成为了辅佐太子的重臣。
朝中风气为之一变,百姓也逐渐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可他的心里,总有一块地方,是空的。
那里住着卢远,住着他们曾经的誓言,住着那份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他站在京城最高的城楼上,眺望着远方。
京城外,沁水河依旧奔流不息,流向远方,流向大海。
江水滔滔,仿佛在诉说着什么。
他知道,卢远从未离开。
他活在江水里,活在文昭的心里,也活在那些被他们拯救过的百姓的笑脸上。
他伸出手,仿佛想抓住什么。
他想,或许,他此生最大的成就,不是功名利禄,而是承继了卢远的遗志。
他回头,看向身后这片他用尽半生心血守护的土地。
这里,有百姓的安居乐业,有国家的兴盛富强。
卢远,你看到了吗?
天边,一轮明月升起,洒下清辉,将大地染成一片银白。
他闭上眼,仿佛听到耳边有水声潺潺。
他愿为江水,与君重逢。
他想,或许,在某个平行于此刻的时光里,他正与卢远在清溪边初见,相识,相知,相伴。
而他,则继续站在这里,守着这份,无法言说的承诺。
他的背影,在月光下,显得格外清瘦,却又格外坚定。
仿佛他与卢远,从未曾真正分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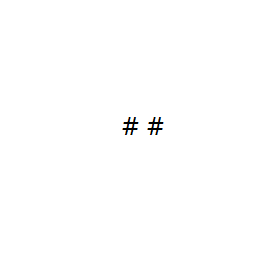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