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主角分别是陈朔王猛的其他类型小说《寒士补天:南北熔魂录陈朔王猛结局+番外》,由网络作家“梦回侏罗纪公园”所著,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本站纯净无弹窗,精彩内容欢迎阅读!小说详情介绍:他指向水面上若隐若现的木船,“表面用青藤覆盖,船底暗置火油罐,每十船用铁链相连,铁链尽头系在两岸的槐木桩上。”他忽然转头,盯着李虎布满血丝的眼睛,“赫连雄的飞骑营,可已绕道泗水?”“五千飞骑,每人带三壶火油,五日前便出发了。”李虎咽了口唾沫,“将军,您真要让他们深入北魏腹地六百里,直扑中山?那里是拓跋焘的粮草中枢,戒备森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陈朔摸了摸腰间的金鹰徽记,冰凉的金属触感让他想起十年前的彭城大捷,“拓跋焘此次倾国南侵,带了三十万大军,后勤全靠中山、邺城两地支撑。赫连雄若能烧掉中山粮仓,敌军必不战自乱。”他忽然望向城南的钟离港,百艘渔船正在雨中穿梭,渔民们顶着斗笠,将成捆的芦苇搬上船——那是为火攻准备的“引火物”。自王...
《寒士补天:南北熔魂录陈朔王猛结局+番外》精彩片段
他指向水面上若隐若现的木船,“表面用青藤覆盖,船底暗置火油罐,每十船用铁链相连,铁链尽头系在两岸的槐木桩上。”
他忽然转头,盯着李虎布满血丝的眼睛,“赫连雄的飞骑营,可已绕道泗水?”
“五千飞骑,每人带三壶火油,五日前便出发了。”
李虎咽了口唾沫,“将军,您真要让他们深入北魏腹地六百里,直扑中山?
那里是拓跋焘的粮草中枢,戒备森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陈朔摸了摸腰间的金鹰徽记,冰凉的金属触感让他想起十年前的彭城大捷,“拓跋焘此次倾国南侵,带了三十万大军,后勤全靠中山、邺城两地支撑。
赫连雄若能烧掉中山粮仓,敌军必不战自乱。”
他忽然望向城南的钟离港,百艘渔船正在雨中穿梭,渔民们顶着斗笠,将成捆的芦苇搬上船——那是为火攻准备的“引火物”。
自王玄谟兵败后,陈朔临危受命,率十万大军屯驻钟离,表面上看是背水一战,实则早已布下天罗地网。
七月二十,暴雨稍歇。
拓跋焘亲至淮水北岸,望着南岸的浮桥冷笑:“陈玄霆啊陈玄霆,你当某家不知这是诱敌之计?
当年在彭城,你靠沼泽坑我,如今又想借淮水玩火?”
他转身对身旁的鲜卑贵族,“传令下去,明日卯时,十万骑兵强渡淮河,先破浮桥,再踏平钟离!”
然而他不知道,陈朔早已在浮桥木板下钉满倒刺,每块木板间留有寸许缝隙,火油顺着缝隙渗入水中,在水面形成薄油层。
更不知上游的拍车船已悄然顺流而下,铁链在水下绷直,只等一声令下。
次日卯时,北魏骑兵开始渡河。
前排战马踏入浮桥,铁蹄刚触木板,便被倒刺扎得惊嘶,骑士纷纷落马。
拓跋焘正要喝止,忽见南岸火光冲天,数十艘火船顺流而下,船头裹着的芦苇遇火即燃,如一条条火龙扑向浮桥。
“不好!
火油!”
鲜卑骑士的惊叫被浪涛声吞没。
火船撞上浮桥,铁链崩断,燃烧的浮桥顺流漂向魏军船队,淮水面上的薄油层遇火即燃,顿时“噼啪”声大作,黑烟蔽日。
“开炮!”
陈朔在城楼挥动红旗。
二十艘拍车船同时发力,投石机甩出的巨石砸向敌阵,每块石头都裹着燃烧的麻絮,落在北魏
着浸过桐油的麻绳,防滑且吸汗。
他突然挥刀劈向石墩,火星四溅中,三寸厚的花岗石竟被砍出深深的缺口。
老周搓着手笑:“咱们在刀刃嵌了熟铁齿,遇甲则咬,比寻常钢刀更利。”
“好!”
陈朔点头,“每月先造两千柄,优先装备霆字营。
另外,弩车的改良如何了?”
老周面露难色:“三弓床弩需三人合力张弦,射程虽到三百步,但搬动不便。
小老儿试着在弩臂装了青铜齿轮,现在两人就能上弦,不过……”他指向工坊角落的半成品,“这铁铸的弩箭太贵,十支箭能换一头牛。”
陈朔沉吟片刻:“箭杆用柘木,箭头用生铁,尾翼换竹片——只要能穿透骑兵皮甲,不必追求全铁。
记住,咱们要的是性价比,不是面子。”
他忽然想起什么,从袖中掏出一张图纸,“再按这个样子,造些‘踏张弩’,让步兵能用脚蹬上弦,射速比手张弩快三倍。”
老周眼睛一亮,接过图纸便往工坊跑。
陈朔望着他的背影,忽然想起八年前在淮阴渡口,自己不过是个后军司马,如今却能调动一州之力改良兵器——这既是文帝刘义隆对北伐的重视,也是他多年战功积累的威信。
午后,陈朔骑马来到彭城郊外的军屯。
大片农田已被分成整齐的方块,农夫们正按“区田法”开沟播种,每寸土地都被深耕细作。
他跳下马来,向正在指导耕种的屯田都尉问道:“今春的禾苗,比去年多长了两寸?”
“回将军,”都尉擦了把汗,“按您说的,每亩施三次粪肥,又在田边种了苜蓿养马,如今麦秆粗得能抵寻常两株。”
他忽然压低声音,“不过有些百姓抱怨,说好好的水田改旱田,怕是要减产。”
陈朔笑了:“带他们去看仓库。”
当农夫们看见屯仓里堆成小山的粟米,去年的存粮竟还剩七成,怨言顿时化作惊叹。
他趁机道:“区田法虽费人工,却能抗旱增收。
等今年秋收,每亩多打三斗粮,你们的赋税便减两成——跟着我陈玄霆,有饭吃,有衣穿,更有铠甲护着家园。”
暮色中返回彭城时,王猛已在帅府等候,案上摆着北魏大军南侵的军报:“拓跋焘亲率五万骑兵,已破我碻磝津防线,正往滑台而来。
前方守将请示,是否固
雄翻身下马,声音里带着从未有过的恭敬,“虎贲营的鲜卑弟兄说,如今咱们既是大夏的兵,便该有个新名号……”陈朔望向校场,阳光穿过旌旗,在胡汉士兵的甲胄上洒下碎金。
他忽然想起在现代看过的民族融合纪录片,那些跨越千年的智慧,此刻正在他手中重现。
“就叫‘河洛营’吧。”
他沉声说道,“黄河与洛水交汇之处,便是胡汉弟兄的共同家园。”
当晚,帅府来了位不速之客——鲜卑老族长拓跋什翼犍。
老人拄着桦木杖,毡靴上沾着洛阳的尘土,身后跟着捧着装酒皮囊的少年。
“陈将军治洛三年,我鲜卑部从最初的五千人,如今已增至两万。”
老人的汉语带着浓重的草原口音,“孩子们开始学汉话,种汉人的麦子,却也没忘了骑射与牧歌。”
他忽然跪地,将酒皮囊高举过顶,“这是用汉地的粟米与鲜卑的马奶酿成的酒,请将军饮下,愿胡汉永不再战。”
陈朔接过酒囊,辛辣的酒香混着奶香扑面而来。
他仰头饮下,酒液顺着胡须滴落,在帅府的青砖上砸出小小的湿痕。
远处,传来胡汉百姓共庆冬至的歌声,鲜卑的长调与汉地的民谣交织,竟格外和谐。
元嘉十一年春,陈朔颁布《河洛令》:胡汉通婚者免三年赋税,鲜卑子弟入太学可袭父爵,汉民从军可习骑射。
诏令颁布当日,洛阳西市竖起三丈高的“胡汉归一碑”,碑额刻着龙与狼的图腾,碑身用汉文与鲜卑文刻着:“昔者,黄帝战蚩尤于涿鹿,合华夏万族;今日,陈公立河洛于中土,融胡汉一家。”
赫连雄亲自为碑刻描红,看着自己的鲜卑名与汉人将领的名字并列其上,忽然对身旁的汉人书吏笑道:“我家拓儿说,将来要考太学的五经博士,你说,能成不?”
书吏大笑:“只要肯下功夫,鲜卑儿郎也能读汉人圣贤书——说不定,还能写出鲜卑人的《孙子兵法》呢!”
春风拂过碑身,将两人的笑声带向远方。
陈朔站在城楼上,望着满城飘扬的大夏旗帜,胡汉百姓肩并肩走过朱雀街,鲜卑少女的辫梢系着汉人式样的绢花,汉家少年的腰间别着鲜卑皮袋。
他知道,民族融合的路从来不是靠政令强行推行,而是在日复一日的共处中,
下去,便能连甲带肉劈开一道血口。
“拓跋焘,还记得淮阴渡口的金鹰头盔吗?”
陈朔追上对方,刀光闪过,削掉其马鞭,“今日若不降,便留在此处喂鱼!”
拓跋焘脸色铁青,深知再耗下去必全军覆没,只得率残部向东北突围。
这一战从卯时杀至申时,北魏骑兵折损七千,连拓跋焘的帅旗都被缴获,史称“彭城大捷”。
战后清点战利品时,李虎捧着魏军的鱼鳞甲来找陈朔:“将军,这甲胄的甲片比咱们的密三成,不过……”他举起破甲刀,“在咱们的刀下,照样跟纸糊的似的。”
陈朔摸着甲胄上的缺口,忽然想起在现代军校时学过的“装甲与反装甲”理论——在马镫尚未完全普及、具装骑兵未成规模的时代,这种针对性的兵器改良,往往能决定战场的胜负。
半月后,捷报传至建康,文帝刘义隆大喜过望,遣使册封陈朔为镇北将军,都督河南诸军事,特许其“便宜行事”。
当使者宣读诏书时,陈朔望着彭城城头新换的“陈”字大旗,忽然想起八年前那个寒夜——从后军司马到封疆大吏,他终于在北府军的体系中站稳了脚跟,更将南朝的防线推进至黄河沿岸。
夜深人静时,他独自来到军帐,铺开最新绘制的“河南四镇布防图”。
滑台、虎牢、洛阳、碻磝,这些曾经的北魏据点,如今已插上南朝的旌旗。
他知道,这只是第一次北伐的胜利,拓跋焘绝不会善罢甘休,而更艰巨的挑战——胡汉杂居的治理难题,正等待着他去解决。
烛火跳动,陈朔提起狼毫,在竹简上写下:“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拓跋嗣善用骑兵机动,却败于地形与后勤;拓跋焘勇而少谋,必不甘雌伏。
吾当以‘飞骑探路、弩车制敌、屯田固本’十二字为要,方保河南无虞。”
窗外,春风拂过彭城,带来泥土的芬芳与战马的嘶鸣。
陈朔吹灭烛火,任由月光照亮地图上的黄河水系——这条孕育了华夏文明的母亲河,此刻正见证着一位穿越者改写历史的征程。
虎啸中原,不过是序幕,真正的硬仗,还在那胡汉交融的洛阳城,在那决定南北命运的钟离渡口。
4 胡汉归一元嘉十年秋,洛阳城朱雀街。
陈朔的乌骓马踏过青石板,车毂碾
。
洛阳百姓将新帝的画像与黄帝、大禹并列,街头巷尾流传着“陈天子降世,胡汉一家亲”的歌谣。
十年后,陈朔站在黄河大堤上,望着胡汉百姓共同开凿的“广通渠”,渠水清澈,灌溉着两岸良田。
赫连雄的儿子赫连拓已成为太学博士,正在编纂《胡汉合志》,书中记载:“大夏皇帝陈玄霆,起于北府寒微,破胡骑于淮泗,融汉匈于河洛,其功在止戈,其德在归一。”
某个秋夜,陈朔独自坐在龙池畔,摩挲着案头的羊皮纸——那是他穿越时随身携带的现代笔记本,扉页上“元嘉草草”的批注早已模糊,却多了一行小字:“历史的车轮可以转弯,但人心的融合永不停歇。”
他望向星空,忽然想起初到北府军的那个寒夜,流星划过天际。
如今,那颗坠星的光芒早已照亮整个中原,在胡汉百姓的笑靥里,在朗朗的读书声中,在阡陌纵横的良田上,续写着属于大夏王朝的传奇。
史书终章,《大夏书·高祖本纪》如是记载:“帝姓陈氏,讳朔,字玄霆,淮南成德人也。
少为北府军司马,及长,都督诸军事,封镇北将军。
值南朝内乱,受禅于洛阳,建国号大夏,改元永光。
帝善用兵,更善用民,创混编之制,开通婚之例,胡汉之隙,至帝而消。
在位二十载,天下大治,河清海晏,实开隋唐大一统之先河。”
而在泛黄的羊皮纸背面,那个穿越者的秘密依然清晰:“我来过,我改变过,我让历史的遗憾,成为了眼前的可能。
所谓天命,从来只垂青于那些敢于直面乱世、缝合裂痕的人。”
秋风拂过,龙池水面泛起涟漪,将星空与灯火揉碎成金。
陈朔放下笔,望向宫墙外的万家灯火,胡汉百姓的笑声穿过夜色传来——这,便是他穷尽一生追寻的答案,亦是一个战魂最圆满的归宿。
6 史笔如刀尾声:史笔如刀千百年后,金陵城的秋雨中,一位白发教授正对着电脑屏幕蹙眉。
他面前摊开的《南北史》复印件上,“陈玄霆”的列传被红笔圈了又圈,字里行间注满问号:“却月阵改良时间与史料矛盾区田法推广早于《齐民要术》成书胡汉混编军制无同期文献佐证”。
办公桌上,考古报告的照片泛着微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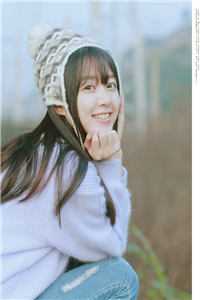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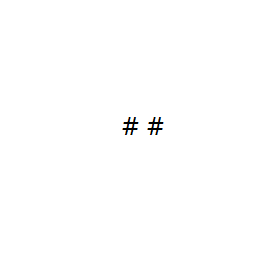
最新评论